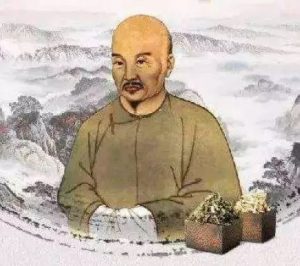| 历史上中医在与热病(疫病)的抗争中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从汉末伤寒,到明清温病,积淀成为临床的基础。张再良教授曾经撰文《伤寒杂病温病一体论》,强调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临床经典。今天面临新冠肺炎的疫情,张教授的文章《疫病临床与伤寒六经》,可以帮助我们贯通古今,启发思路。疫情是战场,现实是课堂。搞懂了温疫与伤寒、六经的关系,面对临床,医者的应对可以更加自如。而通过新冠肺炎的实践,医者对经典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刻。 |
疫病临床与伤寒六经
——兼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治疗中的六经辨证
千百年来,热病(疫病)是人类(也是医学)主要面对的大问题。中医所谓的外感热病,今天看来,主要是指各种传染病,因此广义上都可以称为疫病。温疫在古代频繁发生,带来灾难,也带来医学发展的机遇。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正是在热病临床的反复应对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完善的,中医的临床基础也在热病的应对过程中奠定。
众所周知,中医习惯上将热病分为伤寒与温病两大块,瘟疫和温病靠近。每次温疫的大流行都会留下医家努力的痕迹,只是历史久远,很多已经依稀难辨,所以后人的看法不容易统一。今天重新思考,也许要结合一些现代认识,对问题的把握才容易到位。
时逸人著
疫病的临床有特殊性,伤寒的六经有普遍性。如果认定伤寒是传染病,也属于疫病范围,那么将二者放在一起看就很有意思,我们一定能够从中得到启发。今天遇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爆发,中医应该怎么认识、如何应对,往往会见仁见智,看法不一。历史在现实中会产生回响,既往的外感热病的知识,会自觉不自觉地左右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历史也是一面镜子,温故可以知新。现实是一个契机,借助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表现,联系古人的实践,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医临床治疗的理解。本文对此展开一些议论,抛砖引玉,希望有助于大家的思考。
01、历史上温疫与伤寒曾经对立
古代“疫”的特点,一个是患者病状相似,另一个是致死率高。今天的传染病,其概念更加宽泛。可以说,张仲景和吴又可遇到的都是传染病,但为什么一个是《伤寒论》、一个是《温疫论》呢?对此,我们是否已经充分注意,是否能够深刻理解呢?
从历史过程看,很明显从金元开始,温热(温疫)与伤寒分道扬镳。刘河间倡导“火热论”,指出伤寒“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病”,临床遣方用药偏于寒凉泻火,方用双解散、防风通圣散等。到明末清初,吴又可著《温疫论》,可谓登峰造极,将温疫与伤寒对立,想要在疫病的治疗上开创新的局面。
吴又可
中医的临床辨治,伤寒奠基在前,为什么后面的医家不循常规,要另谋出路呢?这里我们注意到吴又可的叙述。原来在疫病的流行过程中,吴又可目睹当时的医者普遍“误以伤寒法治之”,而患者“枉死不可胜计”,书本和现实矛盾。在事实面前,吴又可观察和归纳了温疫与伤寒的不同,强调时疫是“感天地之疠气……能传染于人”,治疗以“疏利为主”。而伤寒则是“感天地之正气”“不传于人”,治疗“以发表为先”。在吴又可的眼中,温疫和伤寒,泾渭分明,不容混淆。
吴又可敏锐地觉察到疫病的发生,是天地间别有一种疠气所感,与一般的六淫之气不同。从外感六淫到疠气致病,在疫病病因的认识上是明显的进步。吴又可认为《伤寒论》为外感风寒而设,所以疾病的传变和治法与疫病完全不同。吴又可在治疗上进而产生了“一病一药”的设想:“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位加减之劳矣。”可见病因对抗其实并非西方专有,古人对此也曾有意识。
吴又可对伤寒的认识,主要来自《伤寒论》的原文叙述。姑且不论吴又可对伤寒能够认识到何种程度,我们从治法上就可以直接感觉到吴又可面临的困惑。基于以上的归纳,今天我们的思考应该更加深入一些,应该注意到临床的疾病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
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步吴又可后尘,同样对立伤寒与温疫,对温疫的临床治疗作进一步扩展,在治法上别出心裁,制定了升降散及其相关的系列方,提出了以升降散为代表的15首治疗方剂。基本上一个是用清法,所谓“轻则清之”,相关方剂有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复苏饮、大小清凉散、增损三黄石膏汤等;另一个是用泻法,所谓“重则泻之”,相关方剂有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大柴胡汤、增损普济消毒饮、加味凉膈散、解毒承气汤、增损双解散、增损三黄汤等。
杨栗山的临床遭遇与吴又可不同,其将温疫扩展到了温病,但其中的“温病大头六证辨”讲的是鼠疫,此六证乃温病中之最重且凶者,因为仲景的《伤寒论》中无此证治,所以提出伤寒方不可以治温病。也许在这方面,专病专方比较辨证论治疗效更加独到。杨栗山治疗用升降散加减,比普济消毒饮更有效果,同时认为:“惟刘河间《直格》、王安道《溯洄》,以温病与伤寒为时不一,温清不同治,方差强人意。”可见,温疫与温病相似处多,但和伤寒比较,则有明显不同。
温疫在温病中作为分类之一,如《温病条辨》的处理。但也有把温疫另立,分别对待的。不管怎么说,温病宽泛,温疫狭小。如果再把视野放开,伤寒六经基础,温病相对专门。温病的诊疗规律(卫气营血、三焦)可以囊括温疫,但温疫必定还有自己的特殊之处。古人对立伤寒和温疫,强调二者的不同,主要原因是出于对温疫临床治法方药的考虑。吴又可对比伤寒与温疫,临床上有着积极的一面,告诫人们不要因循守旧,面对温疫,必须另谋新法。
02、临床上六经与温疫难以分离
吴又可已经意识到了瘟疫“一病必有一气”的问题,但治疗上却对疫疠之气无奈,只能用达原饮透达膜原,使疫邪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再用汗、下祛邪外出。用六经证治的眼光一看,十分清楚,达原饮是伤寒六经辨治中应对少阳的方法,寒温并用,升降气机,扶正达邪。汗法走表是太阳温散,下法入里是阳明寒泻。
把眼光移到金元时期,北方医家刘河间主“火热论”,倡导伤寒六经传受皆是热证,应对热病以寒凉药为主。以后李东垣主“脾胃论”辨内外伤,有补中益气的甘温除热。用历史的眼光看,他们当时都面临疫病的频繁高发期,用六经证治的框架看,刘河间的方法偏阳明寒泻,李东垣的方法重太阴温补,治法方药仍然不出六经。
金元四大家
这样一看,刘河间、李东垣、吴又可面对疫病,要想有所突破,但方药还是摆脱不了六经。古人的苦心所在,经验独到,但六经还是六经,规律客观实在,不管当事人是否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当然,后来发生的疫病临床不一定能够体现出伤寒六经那么明显的传变规律了。从六经的治法方药看,可以说,六经无处不在,疫病的临床也如此。下面我们另外举几个例子来看。
对于小儿痘证,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讲到:“古方精妙,不可胜数,惟用表药之方,吾不敢信,今人且恣用羌防柴葛升麻紫苏矣。更有愚之愚者,用表药以发闷证是也。(紫闷由枭毒太过,法宜清凉败毒;白闷由本身虚寒、气血不支,法宜峻用温补气血,托之外出。)痘证初起,形势未张,大约辛凉解肌、芳香透络、化浊解毒者十之七八。本身气血虚寒,用温煦保元者十之二三。大约七日以前,外感用事,痘发由温气之行,用钱(仲阳)之凉者十之八九,用陈(文中)之温者一二。七日以后,本身气血用事,纯赖脏真之火,炼毒成浆,此火不外鼓,必致内陷,用陈之温者多,用钱之凉者少也。若始终实热者,则始终用钱,始终虚寒者,则始终用陈。”最后,吴鞠通总结并感叹道:“痘科无一定之证,故无一定之方也……治痘若专主于寒热温凉一家之论,希图省事,祸斯亟矣。”
再看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有关瘟毒吐泻转筋的说法:“上吐下泻转筋一症,古人立名霍乱。”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瘟毒流行,病吐泻转筋者数省,京都尤甚,伤人过半”“彼时业医者,有用参术姜附见效者,便言阴寒;有用芩连栀柏见效者,则云毒火。余曰:非也。不分男妇老少,众人同病,乃瘟毒也。或曰:既是瘟毒,姜附热,芩连凉,皆有见效者何也?余曰:芩连效在病初,人壮毒盛时;姜附效在毒败,人弱气衰时”“活其血,解其毒,未有不一药而愈者”。王清任的解毒活血汤(四逆散、桃红四物汤加葛根、连翘)用于病初吐泻,如果见到汗多肢冷、身凉眼塌,就非用急救回阳汤(四逆汤、理中汤加桃红)不可了,不能因为患者有大渴饮冷而不敢用。
王清任
吴鞠通讲的是痘证,王清任讲的是霍乱,都是疫病。二者在治法上相通的是,或温补气血,或清热解毒,前者太阴,后者阳明,急救回阳在少阴,还是没有跳出六经证治的范畴。据此,我们可以追溯到《金匮要略》中的阴阳毒,用升麻鳖甲汤加减应对,应该是最为简练的表达,阳毒在阳明,阴毒偏太阴。我们再看喻昌对疫病治疗的归纳:“未病前先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上焦升散是太阳的方法,中焦疏利是少阳的方法,下焦攻逐是阳明的方法,贯穿始终的是解毒,体现出专病专药的意思。
临床上如果应对疫病没有特效药,那么治疗还是要回到辨证,用俞根初的话表达:“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诀。”吴又可以后,叶天士、吴鞠通有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的明确提倡,也是针对此类疾病的证治特点,在六经中走出了一条临证的快捷通道,集中体现了寒凉药物应用的规律和技巧,有意无意之间更加充实了六经证治代表的内容。
面对疫病,我们今天的临床还会提到刘河间的防风通圣散、吴又可的达原饮、杨栗山的升降散、王清任的解毒活血汤等,这些都不是特效方,而是后人在六经治法方药上的变通。其实,即便疫病的治疗有了特效药物,临床仍然离不开辨证论治。支持疗法、对症处理仍然需要,现代医学也是如此。行文至此,可以交代一下,伤寒这种疫病比较独特,没有特效药,只能随证治之,之所以能够提供出六经辨治的方法,道理就在于此。
0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治疗的六经解析
当年的伤寒病产生了《伤寒论》,留下六经证治的方法。以后由于疾病的变化,临床的应对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六经证治的内容,补充了临床的治法方药。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积极面对,提出了治疗上的指导方案。用六经的方法来解读,古今对照,可以理解方案中中医治疗的基本原理和规律。
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疗方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的中医证型相对简单,治疗期分为寒湿郁肺证、疫邪闭肺证、内闭外脱证3型,恢复期有肺脾气虚证。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在临床治疗期(确诊病例)中,首先推出清肺排毒汤,然后,轻型分寒湿郁肺证、湿热蕴肺证;普通型分湿毒郁肺证、寒湿阻肺证;重型分疫毒闭肺证、气营两燔证;危重型增加了中药注射剂的选择;恢复期增加了气阴两虚证。可以看出,除了推荐清肺排毒汤,很明显增加了湿热蕴肺证、湿毒郁肺证、寒湿阻肺证、气营两燔证,恢复期补充了气阴两虚证等,供临证选择参考的范围更大了。
配伍清肺排毒汤
从六经辨治的角度看,寒湿郁肺或阻肺证要用太阳温散(与太阴温燥也有关),邪热壅肺证、疫邪闭肺证、气营两燔证要用阳明寒泻(与太阳凉泄也有关),而湿热蕴肺证、湿毒郁肺证则寒温兼顾,归在少阳的位置合适,内闭外脱证用少阴回阳,肺脾气虚用太阴温补,气阴两虚则偏于太阳阳明(肺胃)的凉润。这是从六经证治中提取出来的,更加符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治疗,可以作为临证的参考。这可以视为缩小、简化了的六经治法。看清了其中六经的基础,就容易理解后来温病的卫气营血,再到具体病证的治法,都是一样的道理。每个病证都有自己的特殊之处,都有六经变通的问题,亦即各病有各自的六经(证型)。至于临床多见什么样的证型,今天明白,其实是疾病在背后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为指导方案,需要强调若干要点,以引起临床上的充分注意。但是执行者如果不理解六经证治的原理和规律,就容易墨守成规,不知道变化。比如病初有温散和凉泄的区别,病重有寒湿(湿毒)和温热(热毒、疫毒)的不同,而在病情缠绵、寒热往来、邪正相持之际有和解少阳的方法,在高热伤阴时有少阴的救阴方法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对有关内容有所补充,也是这个道理。六经证治中,温散是麻黄、桂枝同用,凉泄是麻黄、石膏同用,太阳除了温散法、凉泄法,还有调和营卫法。温燥、温补在太阴,寒泻、凉润在阳明,辛开苦降、畅达气机,扶正祛邪在少阳。回阳救逆在少阴,滋养阴液在少阴,寒热兼顾还有厥阴。这样的六经,以法统方,从基本方、类变方到加减方,脉络清楚,层次分明。
04、结语
从现实回看历史,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以和过去的伤寒、温疫与温病对照。面对疫病,专家研究、政府部门出面提供指导性的防治方案,并且随时作出修正、补充。这在古代社会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古代医家必定会有一个更加漫长的摸索过程,个人努力所起的作用其实十分有限。所以,从伤寒病中间能够摸到规律,在《伤寒论》中能够将六经病证的方法固定下来,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搞懂温疫临床和伤寒六经的关系,对我们理解问题有帮助。伤寒非疫的说法,容易造成误解,即伤寒六经的治法方药,用于后来遇到的各种疫病是否有效?很清楚,历史上应对鼠疫,确实伤寒六经乏效。这不是六经不行,而是鼠疫(肺鼠疫)当时确实无药可治。对于各个历史时期医家留下的医著,我们不妨相互对照着看,这才有意思。把整个过程拉成一条线,然后分析各个时空位置上事物的异同。相异的地方,要多思考临床的疾病背景;相同的地方,要提升事物的内在规律。
最后,引用一下当年谢观说过的话:“伤寒与温热、瘟疫之别,尤为医家所聚讼。盖伤寒二字,古人既为天行病之总名,则其所包者广……后世医者泥于字面,一遇天行之病,辄以辛温之剂治之。于是阳明成温之症,见杀于麻桂等方者多矣。”其进一步指出,后世医者“偶遇不寒之疫,遂谓凡疫皆温,本虑医者以辛温之剂误施之温热,转致末流泥温疫之论,不敢复言伤寒。执一定之方,驭万变之病,圣散子杀人,正由于此”。谢观感叹:“有此二误,而伤寒、温热、温疫之争遂如长夜不旦矣。”谢观对时弊的针砭,是否在今天的疫病临床中仍有警世作用呢?
| 作者简介 |
张再良,博士,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长年从事中医经典的教学、临床及研究工作。致力于中医临床证治的通识教育,提出了伤寒出血热、六经九分法和热病四分法,注重从临床的疾病背景理解伤寒、金匮和温病,倡导寒温的融合,主张中西医的一致。近10年在《上海中医药杂志》发表论著20余篇,代表作有《伤寒杂病温病一体论》《伤寒、六经与方证》《六经九分法概述》等。
来源:上海中医药微信,转自“中国中医”公众号(ID:satcm01)/编辑整理:微键